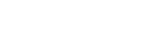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Pit小剧场的舞台上布满了奇形怪状的东西,若不经意,起先你一定会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室:五六个身穿工作服的人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组装工作,正坐在舞台上场处的角落里小憩,惬意地聊着些什么。不过,当你定睛再看时,就会发现原来这里是被各种木箱堆砌出来的一个并不算大的舞台。以色列艺术家阿密特•卓瑞(Amit Drori)的跨学科作品《稀树草原:一种可能的景观》(Savanna :A Possible Landscape),究竟会在舞台上呈现怎样的惊奇?
人性化的视角
作品的名字首先就会带给人们一个疑问:难道这部作品仅仅是描绘南非稀树草原的风景吗?稀树草原,指的是在炎热及季节性干旱气候条件下长成的一种植被类型,它为各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生存环境,而其中有些动物则通过啃食、吃草、传粉、养分循环、种子散播等方式,反过来又造福这种植被。不过,要在一个不足30 平方米的舞台上展现非洲如此广袤无垠的景观,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接下来,由一种奇妙的声音把观众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舞台上那些看似机械化的造型原来都是些充冠乔木的形象,不远处还有野外露营的帐篷。这里的景观稀疏但却不失细腻,仔细端详,就会发现这里汇集了两种不同的力量:一种是类似天堂的景观,在这里生命被再一次塑造;另一种则是可怕的人工自然,人类正在一间孤立的房间里对于“真实世界”进行复制,犹如一个失落的天堂。这部戏是根据一个野外旅行者的经历结构而成的,其中交错在一起的是两个有关死亡体验的故事:一个是有关人的故事,一个是有关象的故事。这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相互映射,形成了极为个人化和人性化的角度。
钢琴与大象的故事
开场,一台古老录音机里传来低哑的声音,讲述着一位母亲和一架钢琴的故事。这是基于阿密特•卓瑞的个人故事——一架有关他死去母亲的钢琴。这架钢琴记载了那些不安的回忆,母亲曾经自行进行强迫性训练,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。而多年后,讲故事的人“袭击”并拆毁了钢琴,以便能够消除钢琴所承载的沉重记忆。然而,经过因果轮回,这位袭击者如今反倒成为了被袭击者,钢琴记忆在他的身上反复出现,显然这些记忆并没有被真正地遗忘。
随着留声机里的话音渐落,舞台上的木盒子被打开了,于是我们突然被带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——这一大象的领地。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,它们至今仍然对人类保留着自己无限的奥秘。不过,人类已探究到越来越多的有关大象的复杂语言和精致文化,以及它们一代代流传的记忆与母系社会的仪式。大象,这个世界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,象征着我们的残忍和无知超过了任何其他物种。剧中,垂危的母象和懵懂的小犊再现着这样一种文化。大象的情节是这部戏的转折点,当母象死去的时候,将这种天堂的景观推向了悲伤的顶点——一个孤独的景观,一座失落的天堂。
跨学科景观
其实,有关剧场的物质环境正是这个世界最好的表征。比如,那些常常隐藏在舞台背后的材料与技术,当把它们置身于前台转换为一部戏的元素或者成为一个戏剧行动时,人们对于那些强调“模仿”、“幻觉”的戏剧传统认知就发生了转变,这也正是当代剧场艺术加以探索的。
在这场戏里,跨学科的工作方式就显得十分有趣,尤其是那些纯手工制作的许多智能小机器。比如在这座大草原里,我们看到了蛇、乌龟、蟋蟀、鸟、公羊、蜗牛、象……它们有些使用金属与木头制作,眼睛却似乎能说话,不断地述说着那个失落的天堂。蜗牛,用一片丁字形的木须、两片圆形的透明有机玻璃,似乎就概括了它的全部身形,而有趣的是,肉身的血脉则由一个集成电路板所替代。大象的生理结构,在戏里被转化为木质手工制作的雕塑,极大地创新了大象的情感与行为方式,若是被拆除,它的身上将会散落下无数的零件。阿密特•卓瑞就是如此钟爱着这种类似于偶戏的创造,这一兴趣从他在耶路撒冷视觉戏剧学院(The School of Visual Theatre )学习时便已生发。他说:“小时候,我常常弹奏吉他,并且想成为一名音乐家。大学里,我学习并涉猎了很多领域,很快便对戏剧着了迷,尤其为木偶戏痴迷。”
因此,从这部戏里,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戏剧,还可看到工程学、机械学以及那些被称 为科学的东西。而如果跳出戏外,就像是在看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摆弄他们的机器人,只是在不经意间演出了一部戏而已。可以这样说,自然与文明的界限在这里被打破了,艺术家们期望赋予这些机械化的动物以敏锐的触觉,借以来反映人类的情感。他们让这些诗化了的机器人,在舞台上重现着人类的心灵:好奇、孤单、空虚、悲观以及亲密......
机械化“角色”
这部作品由五位操作者创造出这些机械化的“角色”。这些“角色”共同的材质是“木”。无论是象、乌龟、蟋蟀、公羊还是鸟等自然界生物,均被艺术家们“解剖”后重又“组装”了起来。于是,观众可以清晰地看见它们身上那些灵动的关节以及无数的铆钉。同时,其身体内部由于安装了集成电路板,那些颜色各异的电路,就如同人类体内的血管一般承载着它们的命脉。操作者只要手持无线控制器,便可实施它们在这片草原上的运动。观众也仿佛参与其中——我们目睹着他们如何“操纵”它们的命运,就如同人类看着自己一样。
稀树草原以一种十分简约的方式被呈现出来,一系列的木盒子呈现在舞台上,构成了地形、景观、地域的外轮廓线。另外这些木盒子还作为投影的界面,并且邀请观众运用他们的想象力,与投影共同去完成一个想象的画面。于是在这部戏里,人的视角由此被分成了几个核心因素:创作者的状态、观察者的状态、操作者的状态、互动时的状态。当然,表演者们仍是这些人工自然的创造者,这种与机械动物的互动在以往戏剧舞台上是极为少见的,同时它们也是极为脆弱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与自然那条古老的边界线连成的这一虚构的生态景观,也反映出人类自己对于自然而言的那个“又爱又恨”的角色。